早在1999年,平野启一郎就凭借小说《日蚀》获得第120届芥川奖。时隔近20年,他的写作风格不断转变,一再成为日本文坛的话题人物,也揽获了其他诸多奖项。但因为此前缺少译介,今年夏天,当这位日本作家出现在上海书展时,对于更多的中国读者来说,他依然是一位新人。
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
认识平野启一郎,还要从他的成名作《日蚀》说起。一则,它在作家的作品中依然尤为独特;二来,它也是作家在此后的写作中不断探讨的有关“分人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的酝酿和发端;再者,它是平野目前仅被翻译成中文的两部作品之一。
《日蚀》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5世纪的法国,作者以一个在巴黎学习托马斯神学的学生作为叙述者,用一种长篇日记体回忆了他神奇的经历:为了寻求费奇诺的《赫密斯派文献》,他前往佛罗伦萨,在距离里昂不远的一个村子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堕落世俗的僧侣、狡猾的畸形男人、纯洁的聋哑少年以及古怪的炼金术士等等。接下来,他跟着炼金术士的步伐,眼见了双性人被冠以女巫之名施以火刑……作者以此描绘中世纪末期神权与世俗社会对立、融合的景象。
写作时,平野启一郎只有23岁,正在念京都大学。初到大学第一年他就经历了阪神大地震。那年春假往返九州时,从姬路到东京的新干线停运,只能坐飞机,回程就刚好在大阪机场看到了“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新闻。这让他产生了一种末世感。他希望能用一种非日常的书写排解日常中的忧郁,或者说,是去对抗时代的闭锁性。
《日蚀》
于是,他选择去写炼金术,去写中世纪的法国。因为那个由一神教、战争、黑死病填充的时代,在他眼中同样有一种末日将近的氛围,和90年代中期,泡沫破裂,经济低迷,旧的价值观解体,新价值观还未建立的日本非常相似。他说,在那样的形态下,宗教要通过惩罚别人来确立自我、体现自我,比如经过磋磨、虐待巫女的身体来寻求一种价值观。而中世纪宗教性的炼金术,同样体现了当时时代的思想趋势。整部小说的主题和思考以及内心描写都不同于其他当代日本作家的风格,因此,有评论甚至认为:“与其说这是日本作家的作品,不如说这更像欧洲作家的小说。”
平野接下来发表的小说《一月物语》同样是反时代的,小说的主人公以自杀的日本明治诗人北村透谷作为原型:透谷一方面追求东方古典式的自然神秘一体化状态,另一方面则是信奉西欧的恋爱至上主义,并期待着现实中恋爱的能动性。“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吸收了西欧的很多思想,但实际只是吸收了表面,没有真正地进入日本文化中。《一月物语》的主人公就处在这样新旧交替的时代,很难消化接受新思潮。”与《日蚀》里西洋古典的背景不同,在这一次的叙述中,平野融入了中国古典元素,从蝴蝶与梦的关联,到对唐代李贺诗句的引用等等。
“通常来说,一个小说家在其第二部、第三部作品时,其守备范围就已经明了了。按照从前的说法就是,创作风格显现出来了。然后使其创作风格稳步发展,主题与方法的坐标轴逐渐稳定下来,读者们便开始安心地关注其走向。赞叹也好,沮丧也罢,都是在其风格限度内。”三浦雅士曾在撰文评论平野启一郎的写作时,提到过以上这种在东西方世界或多或少已成为文学习惯,甚至是文学制度的存在。他的言下之意是,平野的写作,并不在这一范围之中。对他而言:“平野启一郎还是个谜一样的作家。”
他所不能理解之谜,是平野继而发表的小说,2002年的《葬送》,2008年的《决口》,前者2500页,取材于肖邦与德拉克罗瓦,是一部近似标准的艺术家小说,后者1500页,是以21世纪的网络社会作为背景写作的犯罪小说。还有其间出版的那些充满实验性质的短篇集:《高濑川》《滴落时钟群的波纹》,同样“扩散与充实”。“一方面,正当你认为他采用了坚实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手法时,另一方面则展开了令人不得不想起现代诗破天荒的语言实验。这位作家就是思想犯。”他以为,这些作品的出版,“就像是平野启一郎在嘲笑我们的困惑”。
三浦雅士的困惑一定不是他所独有的,这或许也是平野常在作品发表之后成为日本文坛话题人物的原因所在。但作家本人也同样认为写作中呈现出悬殊的手法和表达,使他的作品无法归纳,甚至毫无关联吗?
并非如此。他告诉我们,如果《日蚀》中以太阳作为象征,那么《一月物语》的象征就是月亮。它们之间的默契在于时间,《日蚀》中谈到资本主义,时间如直线,指向利己主义;《一月物语》的时间则是环线,主人公被卷进日升月落的循环,一系列的故事才得以发生。《日蚀》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如何产生,又如何变化;《一月物语》是从日本的角度重新看待人与神。再到后来的《葬送》,是公民社会建立起来、人和神的关系不再重要以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变得怎样,以及个人的身份认同。
在这当中,平野始终想要追索的问题是:对于个体的人而言,“自己”究竟是什么?这是从《日蚀》就开始了的一种抽象式的思考。直到后来的小说《最后的变身》,这种思考才在写作中变得具体。他开始就“真正的自己”与“暂时的自己”,去考虑自我同一性的问题。《没有脸的裸体们》,探讨了“网络上的自己”与“真正的自己”“社会中的自己”之间的一种变化关系。到了写作《决口》时,他感到“个人”的概念已经走到了极限。如果继续使用这个概念写作,将不会再有新的发展。于是在后面的《曙光号》中,就提出了“分人主义”的概念。
平野启一郎认为,人有“复数的自己”。对于亲人、恋人、上司等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自己”都是真正的自己。这是人与具体的社会接触中变成的样子,而非简单的不同面孔,不同于过去“个人是不可分的”认知。因为现代社会职业的要求,在日本,人们曾长期以来都是一辈子只做一个职业,但是现在,复数的自己可以在社会的变化中更好地生存,通过“复数”来做不同的事情,这样即使一个做不成,另一个做成,也还是可以实现自己。他所希望在小说中探寻的,就是人在现今的社会中应该怎么活。
而作品的形式,无非是同一思想的变体。就像他解释自己写作短篇,是因当时的时代,对于要创作一部构架宏大的长篇来讲,有一些过于纷乱。虽然其中存在实验性质,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探究文学以外的,现代艺术的思路在小说中有多少可行性,但核心依然延伸至“分人主义”。再后来,平野开始刻意在作品中回避掉“分人”这个词,不再用它解释分人主义,以达到一种模糊的效果。比如2016年出版的小说《剧演的终章》,里面就根本没有提到“分人”,但这个概念却依然作为小说的背景存在。
平野启一郎曾经说,“分人主义”对他的影响极其深刻,甚至决定了他基本的人生观。或者,这已经不再是他力图表达的观念而已。就像三浦雅士谈到其作品主题、方法的扩散与充实时说:“除了用异常一词来形容外别无他法。这是一个作家不可为之事。不,如果结合社会规范,更为正确地来说的话,这又是一个作家必做之事。因为作为小说家的同一性尚未确立,必然存在复数的平野启一郎。”
面对复数的自己
——专访平野启一郎
“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创作观在我看来需要一些改变,我想要创造一个偏‘分人主义’的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从《日蚀》开始,你一直在书写不同风格的作品,其中也包括很多实验性的尝试,在这当中,什么是你一以贯之,甚至可能会在将来的作品中持续讨论的问题?
平野启一郎:对我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每一个现代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怎样才能做真正的自己?所以我引入了“分人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我从欧洲近代的一个哲学概念中阐发出来的,是对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以及一个人如何才能做自己的一种现代性的阐释。它基本上就是我创作的中心。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平野启一郎:“个人是不可分的”这个理念,是近代社会的基础。但是现代社会人们为了跟不同的人产生交际关系,就会产生很多个“自己”存在,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人的不同的表面,是分裂出的不同面孔,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人们有“复数的自己”,对于亲人、恋人、上司等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自己”都是真正的自己。复数的自己可以在社会的变化中更好地生存。人们经常是通过复数的自己来做不同的事情,这样即使一个做不成,另一个可以做成,还是可以实现自己。
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创作观在我看来需要一些改变,我想要创造一个偏“分人主义”的世界。人最早从猿,四只脚,变为人,两只脚,这种历史过程固然是不能改变的,但当我们面对接下来的社会时,却可以使用“分人”这个概念。因此,在30岁左右的时候,我以此为中心写了一些小说。直到最近的作品《剧演的终章》,里面虽然没有直接用“分人”这个词,但这个概念依然始终作为背景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在早期阶段的作品《日蚀》《一月物语》里面,想要表达的也是“分人主义”吗?似乎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
平野启一郎:与其说我是想要以小说形式来表现它,不如说是通过小说一直在进行思考。早期的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概念,但那时已经开始思考“我是谁”,对个体而言,“自己”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是已经在酝酿这个想法了。
《日蚀》的背景设定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里面谈到人与神、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以及怎样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月物语》是将个人投入神秘主义的背景之中,从日本的角度重新看待人与神的关系。欧洲的个人观念源自一神教,人们需要以统一的自己去面对仅有一位的神灵,到了近现代社会,有关个人的思潮开始萌芽,神消失了,统一的自我分裂产生出复数的“自己”。“分人主义”实际上就建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它对应的就是我所设定的小说的时代背景。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最初的几部作品都将背景设置在法国,是有什么特殊的情结么?
平野启一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三岛由纪夫,而他创作的主要灵感来源就是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文学。为了更深入地读他的作品,我慢慢地接触了欧洲的文学作品,其中特别喜欢19世纪的法国文学。相比读一些身边的文学作品,读法国文学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己,也比较向往那种文学风格。虽然物理上,我的身体是在日本九州长大的,但精神上,我其实是受到以法国为代表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所以在写《日蚀》的时候,就以法国为背景了。另外,日本近代以来受到欧洲的影响非常深刻,欧洲作品在日本的出版也比较强盛,可以经常读到,因此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有评论说《日蚀》不像日本作家的作品,更像是欧洲人写的。这不光是因为背景、人物的设定,还因为你文体的选择。
平野启一郎:用日常的普通文体,好像不太符合我想要反映的风格,我觉得应该以一种稍微有点艰涩,或者说特别一点的文体和语汇来描绘我的作品。虽然日常的文风和写法,有时也会让人有一些深刻和丰富的体验,但我希望还能超越这样的体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很多作家用日常的文风写作,读过之后我觉得刺激不够,好像不太能得到满足。而那个时期,我更侧重于“自己想如何写”,所以就用了不太一样的风格,至于读者能不能接受,当时都没有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在小说中插入空白页又是想表达什么呢?
平野启一郎:小说的背景定位在中世纪末期,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当时在人和神之间,神比较重要。人会接受到像“神谕”这样一种绝对存在的概念。神秘主义会营造出各种各样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我其实是为了那两页空白,才写这篇小说的。我经常想要在作品里实现一种用语言不可能完成的语言,当一些内容不能通过语言很好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就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实现传达,这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非常大的动机。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你的很多作品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但是你所作的大量实验性的写作,我们也有所耳闻。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不会只是一种对独特性的追求吧?
平野启一郎:其实还是为了尝试去更好地处理现代的人和社会的关系。社会不停地发展,且越来越快,90年代以后互联网兴起,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近。19、20世纪作家传统的写作方式不会去考虑这些当时尚未出现的问题和情况,而现在,作家和读者都需要一种崭新的书写和思考方式。当然,也有些作家不太愿意去认识新的变化,还是觉得19世纪的文体很好,这当然也可以。但继续写下去,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越来越不顺畅,因为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学虽然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传统,可以去追溯之前的历史,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它很快又成为历史,这是一个越来越完善的过程,但与其不停地去追溯历史,还不如更注重现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现在的文学应该怎么去写。实际上,光是我自己去写,还不能完成实验,只有作品发表之后,将读者的反馈回收形成最终的结果,才是一个完整的实验。
三联生活周刊:但如今,你的作品已经逐渐脱离实验性,走向通俗易懂。这又是为什么?是考虑到读者的反馈了吗?听说读者的群体真的比以前规模更大了。
平野启一郎:最近写的长篇小说变得比较通俗,其实也是多亏了之前做的那些实验,这也是一部分实验成果。经过那些实验,我觉得“有趣”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什么是有趣的,什么不是有趣的,这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我现在在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所以写的时候会偏向通俗易懂,为了让人读到之后觉得有趣。读者比以前规模大,可能也和我还在玩儿音乐,开过很多现场的摇滚音乐会有关。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在这个让写作走向通俗的过程里,需要警惕自己的作品从“纯文学”走向“大众文学”吗?
平野启一郎:“有趣”很重要,但不能单纯为了有趣。我个人理解的有趣,可能偏向于认知科学方面的理论,也要将它放在一个哲学范畴、分人主义的范畴里面去解决。我在考虑“分人主义”的时候,关键还是希望能探索和解决人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怎么活的问题,我希望读者在读过我的作品之后,能够获得一些想法,比如我应该这样活,或应该那样活。我觉得读者多了并不意味着倾向于通俗文学。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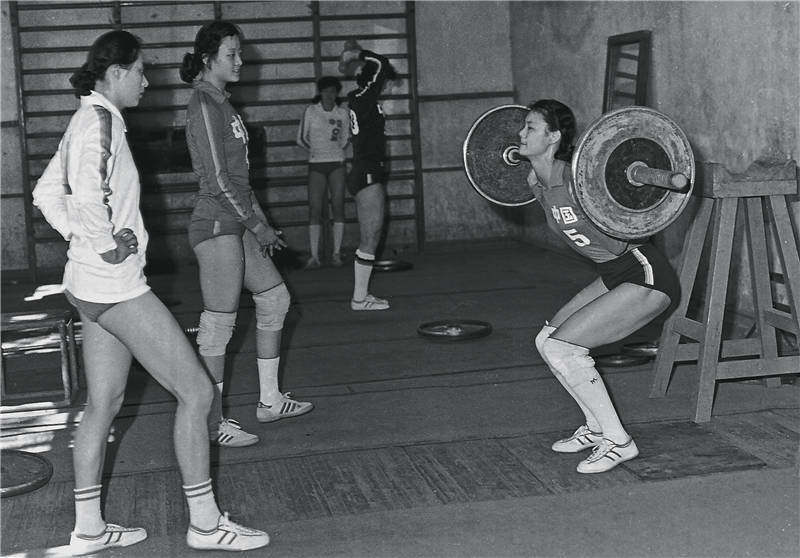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