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于北京逝世。这位作家中的作家,“最后一个浪漫派”,消失了。
沈从文的目光
到凤凰寻沈从文,去看了“森林实景剧”《边城》。边城不在凤凰,在川湘黔交界的茶峒,距离凤凰还有几小时车程。《边城》成为凤凰的名片,因为沈从文生于此、长于此,他的作品也就成为此地场所精神的一部分。

我下榻在古城边的虹桥,剧场在城另一头的凤凰大桥附近。夜幕中,我从虹桥出发,沿沱江岸边走,在用两排石头桩搭成的“跳岩”那里过河。过了河,沿着江岸,绕过古城中心——沈从文的故居在那里面,一路往凤凰大桥走。沱江两岸客栈民宿、咖啡厅酒吧灯火璀璨,游客如织,全然不是沈从文到过这里时的凤凰。我身处的这个小山城已是个商业化的旅游风景区,不仅沱江两岸,连古城深处石板路小巷子两旁的店铺都几乎无一不是为招徕游客而做的生意。人也不完全是淳朴的想象——踏入一些宅院里、寺庙里,有时会有先生动辄拿出一本功德募捐册子,让你往上填要捐的钱数,好几栏项目,前面都是整整齐齐的百元量级,可能是他们自己填写的,用来蛊惑人。一切和沈从文在这些蜘蛛网般的迷宫中穿行时,令他着迷的劳动者的传统手工艺营作不同了。不禁怀疑,是否还能在凤凰寻找到沈从文?
那晚沿着沱江河岸一直走了很远,人语声渐渐稀薄,夜幕严严实实将所有包围起来,这时两岸的灯火已逐渐黯淡下来。岩坎上有一家米粉店,在沿几级台阶上去的地方,我走进去,问老板剧场怎么走。她说:“一直往前走,经过第一座桥,再走,看到第二座桥,往上走。”往“上”走——我还难以清晰地在意识中理解这个方向词,只觉得新鲜又古怪。
一直向前走去。走在这条岸的路上,有时抬头看得见高处的确还有一排吊脚楼和一条并行的小街,比方才问路的米粉店还要高,但看不全,被岸边这排房子遮住了,不像那个米粉店,看得到全貌,几步台阶能走进去。那条平行的路时隐时现,有时完全看不见,侧耳细听也听不见从视线背后传来什么声音,只偶尔有一两声犬吠。如若在上面来回走过,熟悉那儿,此刻就可以一边在江岸行走,一边浮现出那条街的印象。看到了第一座桥,行进中,逐渐已走离游客聚集的古城中心。流溢的灯光变得星星点点,夜的厚度开始沉重,随着夜凉,渐渐压在我背脊上,有点凉飕飕。我加快脚步,侧耳倾听,沱江两岸轮廓黝黑的重山里传来鸟儿们的鸣叫。我辨认不出是哪种鸟,只觉得那悠然停顿、等回声沉寂后再来一声的缓慢节奏很适合在夜幕里鸣唱,不像清晨的鸟儿们那么轻快婉转。那声音从我看不见的远处传来,漂浮在沱江水面上,却增添了此刻的沉静。几乎已没有人影,目光所及还能看见的岸边房子,都是清水楼,光秃秃的混凝土架子,无人住。它们不是被荒废,而是在建设中——资本拓展的边缘。
然后看见了高高架在江上的凤凰大桥。从我站的地方往上看,大概有十层楼那么高。我在黑暗中找不到可以上去的路,一时产生了那是座空中之桥的幻觉。一个身影从黑暗中渐显轮廓,慢慢看清,是个女人,正在江边把衣服拧干,脚边还有洗衣的塑料盆。在这有点偏僻荒凉的角落,见到一个人总是要凝神看一会儿。我向她问路,她指了那条藏在路边的山路,“向上走”。我就向“上”走去。那条小路蜿蜒藏于树林中,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很幽静。上了几十步阶梯,小径将要转弯处,我站在半山腰回过头往下看。刚才我走过的那条沿江岸的路已被一片树林遮挡得完全看不见,唯有鸟声依旧,从无法辨明方向的黑夜深处传来,仿佛下面并不存在着另一条路、另一个世界。我却知道那里有条路,因为我从那里走过,还想着刚才在那“下面”向洗衣妇女问路的情形,从而“看”见她还站在那里,拧好了刚才那件衣服,又弯腰拿出塑料盆里剩下的衣服来拧。
再往上走一步,拐过弯,树林之外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既想碰到行人,又害怕碰见任何人,就在这小径中飞奔了数十步,一边想象着尽头会是什么,但想不到。再拐过一个弯,眼前突然看得见前方高处的一点光亮了。耳畔传来高处的隆隆回声,是车行于道路的声音。在时而遮挡不见的层叠空间里,牵引着想象和思绪的总是声音。登上最后一步台阶,站上凤凰大桥,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正在我眼前向左右两个方向延展开去。那马路旁仍然是山,几辆公交车从我面前驶过,马路边走着熙攘人群。从未想象迎接我的将是这样一番热闹、现代的人间景象,就在之前的那段山路上,还于黑暗的幽静中产生过置身于荒野的孤独感。过了马路,走向霓虹灯闪烁、宾馆林立的剧场所在地,自然开始想象自己正于“高处”行走——沱江水和沿岸酒吧林立的古城已完全看不见,但我知道,它们正在我的“下面”流淌和热闹着,酒吧、客栈里的游客、米粉店老板和拧衣服的女人都在忙活着自己的事。我在那里行走过,从那里走山路上来,待会儿还要再回到那里去,沿途返回——这个此地独有的俯瞰视角,就是这样进入我的意识的。行走在这上面的人,也都一定于某些时候在下面行走过,和我一样,却不知他们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想象。待到看完《边城》往下走,在那条山间小道上,渐渐看不见虹桥上面的这个世界。然而沿着沱江岸走时,我想着在虹桥柏油马路和车流中行走的情形,想着不久前看到的鳞次栉比的宾馆楼群,就知道它正在“上面”存在和躁动着。在层叠的重山之中,“高处”与“下面”的意味非常自然。
正是在那个时刻,我多理解了一些沈从文。在那段夜路上,我隐隐约约看见了他。凤凰无论如何随时代变迁,河水仍在流淌着,树林里的鸟儿还在清晨和夜晚以它们古老的习惯鸣唱着,那声音把人带入一个悠远的过去。那些往许多方向延伸着、时隐时现的路,因为新时代的建造改变了许多,也新造了很多桥,但它们在重山之内这一点,就让它们不会变得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方作为故乡的水土,内生性地一日日长入了沈从文的头脑中。他开始写凤凰这个地方,写边城,写湘西时,已离开此地一些年头。他不是在凤凰写的凤凰,也不是在湘西途中写的湘西,而是到北京之后,或者再之后辗转于昆明、上海和青岛时所写。他书写的是他记忆里和想象中的凤凰。直到1934年1月,他在返湘旅途中每天给妻子张兆和写信报告沿途见闻,他才和阔别十年的凤凰小城重逢。
在凤凰,再次温习《边城》。沈从文会这样描述这座水边的小山城:“住在城中较高处,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纤夫……船来时,小孩子的想象,当在那些拉船人方面。”他会让声音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探路,翠翠就是在这样的牵引下出场的,“蓬蓬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黄狗“忽然醒来发疯似的乱跑”,它的主人翠翠骂狗,一会儿也发现了声音,跟着黄狗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笔下人物的心思也流转着,翠翠第一次见到只听过其声、未见过其人的二老,心想“正像是不肯把这人想到某方面去,方猜不着这来人的身份”。穿行于凤凰的水边和重山中,沈从文的目光开始从这些句子里隐约浮现。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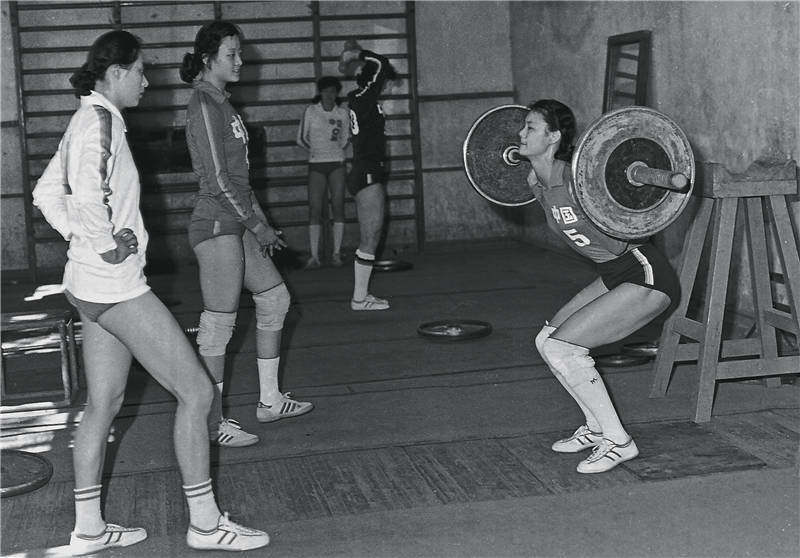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