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4月11日,默克尔抵达雅典访问,就希腊重返国际债券市场问题与该国政府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这可能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时刻:身为波兰外交部长,我不担心德国的权势坐大,相反更担忧它的领导人放任不理。”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aw Sikorski)在媒体面前显得精疲力竭。
那一天是2011年11月28日,蔓延了两年之久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逼近新的临界点。西科尔斯基从华沙匆匆飞往柏林,恳求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政府领导人默克尔批准购买更多的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债券,以帮助这些被恐慌笼罩的东南欧国家获得一点喘息时间。战地记者出身的西科尔斯基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场体验过枪林弹雨,但他告诉自己的朋友、美国政治分析师彼得·考伊(Peter Coy),自己最惴惴不安的还是等待德国总理宣布最终决定的那几个小时。
默克尔不苟言笑的脸孔出现在了摄像机镜头前。当着法国总统萨科齐以及十几个欧盟成员国高级官员的面,她以严厉的语气宣布:“我们认为这(购买更多债券)既不是当务之急,也不是债务国真正需要的。”“没有理由要求德国纳税人为其他成员国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按照她的看法,负债国必须首先确认自己积欠债务的总额,接着向同意提供纾困帮助的国家做出事无巨细的保证,承诺会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削减公共支出以增加财政结余和偿还能力,并接受在整个紧缩周期内的国际监督,随后才能获得所需的帮助。至于波兰人热切盼望的短期流动性,默克尔借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之口做出了回应:“喝海水并不能解渴。”
2011年之后的十年里,逐步恢复元气的波兰开始和匈牙利一起成为默克尔“更大的欧洲”战略的反对者,并在欧盟财政预算的制订以及移民政策问题上频频向柏林射出冷箭。默克尔的回应同样显得强硬:2017年12月20日,欧盟委员会(联盟最高行政机关)以波兰政府推动的司法改革“未能维护欧盟的民主价值观”为由,要求援引《里斯本条约》第7条(俗称“核条款”)对其加以制裁。到了2018年,拒绝承担接收中东难民义务的匈牙利政府也因为“核条款”,在欧洲议会被置于制裁诉讼程序中。不过,高高举起的“大棒”从未真正落到这两个东欧国家的政府身上;反倒是默克尔本人在2020年12月的欧盟七年财政预算框架审核会议上,赞成对匈牙利和波兰网开一面,使其可以分享复兴资金援助。
面对债务危机深重的东南欧国家,默克尔坚持紧缩优先、寸步不让,直到最后关头才松口给予救助,却没能收获感激之情,反而给本土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留下了“以大欺小”的话柄。在中东难民的收容和救助问题上,德国率先垂范,主动带头承担了最大份额的义务,结局却是更加广泛的质疑和攻讦。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作为区域合作组织的欧盟与其“双引擎”之一德国之间的关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微妙难测。这种无处不在的张力,并不会随着默克尔的退休骤然消失。

2015年10月25日,持疑欧主义立场的波兰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赢得议会选举,其党魁贝娅塔·希德沃(举手者)将成为波兰新一任总理
失落的“中欧”理想
对在“冷战”时代的东德度过了青年时光的默克尔来说,类似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前东欧阵营国家,本来可以给她带来显著的亲切感。而在她的政治领路人科尔的设想中,东欧也应当是德国重点经营的方向。
从1995年到2003年,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卫星国、或者位于两大阵营缓冲地带的16个“新欧洲”国家,作为欧洲一体化扩大的重要步骤,分四批加入了欧盟。在地理上,它们散布于北欧、东欧和南欧;但乐观主义者会更多地提到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中欧”(Central Europ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这16个国家中有7个曾经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个结构松散,拥有多个主体民族和多种宗教、文化的古老中欧国家,尽管长期存在治理效率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暗合了欧盟对其内在精神的期许。如同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言,一种“中欧化”的理想将使这些新入盟国家摆脱莫斯科长久以来对其政治和经济的深远影响,形成一个以柏林为中心、与巴黎并驾齐驱的经济-文化圈。
但这一理想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经历接二连三的坍缩。两德统一后的前15年,德国忙于完成自身经济与社会的重新整合,并未将主要精力和资源倾注到经营中欧蓝图上。而以维克托·奥尔班(匈牙利总理)为代表的一批当地政治人物,迅速在“重新发现主体性”的旗号下建立起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将自己领导的政党摆在政治光谱的中间偏右侧。
换言之,在德国希望扩展影响力的领土上,获胜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中欧化”理想,而是从“冷战”意识形态废墟中爬出、借助激烈的民族情绪获得新生命的本土主义。这种本土主义倾向,随后就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经济:早在1998~2002年第一次登台组阁时,奥尔班就展现出了凭借中央政府的统一调控措施解决赤字和通胀问题的倾向。这种政策基调在当时招来了普遍质疑,但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却重新获得了广泛认同。2010年至今,奥尔班及其政党连续赢得三届匈牙利议会选举,显示出保守的本土主义确有其民意基础。

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在21世纪初曾任波兰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默克尔在2011年拒绝了他提出的购买更多主权债券的请求
作为奥尔班的长期批评者和政治对手,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位出生在匈牙利的亿万富翁对中欧理想的失败做出了反思。在索罗斯看来,柏林本来应将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化转轨看成一项政治事业,而非获取暴利的途径,但上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摧毁了这种愿景。进入匈牙利和波兰、捷克的外国资本单单投资在了可以迅速获得收益的工业和金融领域,对基层社区的重构和收入均衡的维持却投入不足,建设开放社会所必需的财政和思想资源因此出现了严重赤字。实际上,德国唯一有求于东欧的生产要素仅仅是廉价劳动力——到2050年,欧盟第一批成员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8.7%。为了使这些创造财富的能力日益趋缓的老年人能够继续享有可观的社会福利,西欧、尤其是德国急需引入工资标准相对较低的东欧劳动力。对亲历过“冷战”时期经互会贸易模式的老一辈东欧人来说,这不啻一种新的国际剥削:过去是东欧以农产品和特定工业制成品弥补苏联的产业结构缺陷,如今则是东欧以廉价劳动力支撑西欧国家的高福利社会政策。两者在道义上毫无高下之别,都不过是利益交换,中东欧对西欧毫无亏欠。
诚然,东欧新入盟国家从欧盟的共同预算政策中获益颇多:这也是默克尔最引以为豪的政策“杠杆”。在上一个七年预算周期(2013~2020)里,匈牙利GDP总量的4%和欧盟的预算拨款具有直接关联,全国55%的公共投资受到欧盟、尤其是德国预算拨款的支持(波兰则为60%)。在欧亚集团2019年夏天发起的民调中,有84%的匈牙利人和86%的波兰人对一体化的总体影响持认可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欧诸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默克尔倡导的国际义务——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东欧诸国的本土经济和平均收入水平增长相较预期明显偏弱。截止到2019年,只有捷克的人均经济产值达到了西欧发达国家的80%,匈牙利和波兰则为63%,更弱的保加利亚只有43%。而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外国资本的出走以及劳动力需求的放缓,东欧各国政府感受到的压力甚至比西欧更加突出。当这种焦虑感与中东难民的大举涌入同时出现时,结果可想而知。

2011年8月19日,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一名交易员紧张地关注着欧洲股市的暴跌状况
在东欧诸国、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民族主义者看来,“阿拉伯之春”以及接踵而至的中东政局动荡与他们本无关联,美国调控政策的失当乃至西欧诸国的应对滞后才是始作俑者。东欧既已通过输出劳动力、让渡部分内政自主权以及开放国内市场等途径“偿还”了预算转让的实惠,便没有理由再被分配与本国战略利益无关的人道主义义务。更何况,类似奥尔班内阁这样从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土壤上崛起的新政权本身便担负着保障国内就业、维持收支平衡的任务;一旦允许中东难民落脚,势必增加开支负担,连带还将影响匈牙利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水平。该国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业密集区选民因此迅速成为抵制安置难民的急先锋。在2015~2016年,匈牙利政府更是耗费了8.83亿欧元的巨资,沿着南部国界建立起一道175公里长、由铁丝网和边防巡逻队组成的防越界隔离带,防止难民经巴尔干进入该国境内,并要求欧盟承担一半的费用。
维克托·奥尔班的崛起并非单一案例。2015年,右翼保守派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时隔八年卷土重来,赢得波兰议会选举。2017年10月,奥地利中间派“大联盟”政府因内讧而瓦解;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极右翼自由党与中右翼人民党联手拿下了组阁权。紧接着,人称“中欧版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平民主义者巴比什当选为捷克总统,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同样组建了由疑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主导的新内阁。当对多边主义模式的失望和对“默克尔的入侵者”(这是奥尔班对叙利亚难民的蔑称)的恐惧结合到一起时,受伤的总是柏林。
在欧盟的东部和南部,一道无形的新“柏林墙”正在重新形成。来自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疑欧主义者们组成了事实上的地区同盟,一方面继续要求获得联盟的预算转让,另一方面则抵制一切分担人道主义义务和改善司法、舆论环境的改革。面对这种“软抵抗”,默克尔能做的很有限,因为南欧同样存在着怀疑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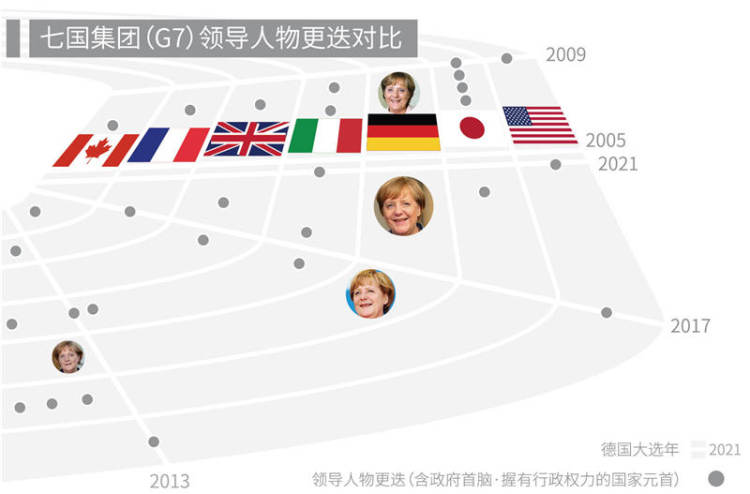
(郜超 绘制)
来自希腊的不满
如果说柏林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分歧主要来自中东难民问题,那么围绕希腊债务危机救助问题产生的风波就属于另一层面:德国这个全欧盟民族主义色彩最弱的成员国,在南欧国家眼中成为了恃强凌弱的代表。
2017年初夏,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已有近十年之久的希腊政府宣布和德国达成共识,接受默克尔等欧元区领导人提出的“欧盟历史上干预力度最大的救助方案”,以换取为期三年、共860亿欧元的纾困资金。欧元区各国要求希腊政府将其最具价值的公共资产(总额500亿欧元)注入一只设在卢森堡的私有化基金,由欧盟监管,将出售这部分资产的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希腊纾困方案的核心内容,正是默克尔一向倡导的量入为出、厉行紧缩的政策。它所包含的削减开支和资本管制条款意味着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希腊经济将严重缺乏流动性,从而影响到其复苏的前景,普通国民的福利待遇也会遭受重大冲击。正是针对这种带有惩罚性的紧缩措施,南欧集团流露出了公开的不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在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的前五年,德国实际上是以南欧国家的大规模贸易赤字作为隐性代价,实现了自身出口顺差的最大化。但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进入南欧的资本出现断档,德国却没有对本国的外贸政策做出相应调整,反而要求南欧国家厉行紧缩,自己也控制消费,减少采购来自南欧的商品和服务。结果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失业率在短期内出现暴增,随后还须进一步接受条款极为严苛的纾困方案。而德国自身在欧盟自贸区这个传统出口对象之外,开辟出了美国和东亚的新市场,继而对南欧国家的偿债方案做出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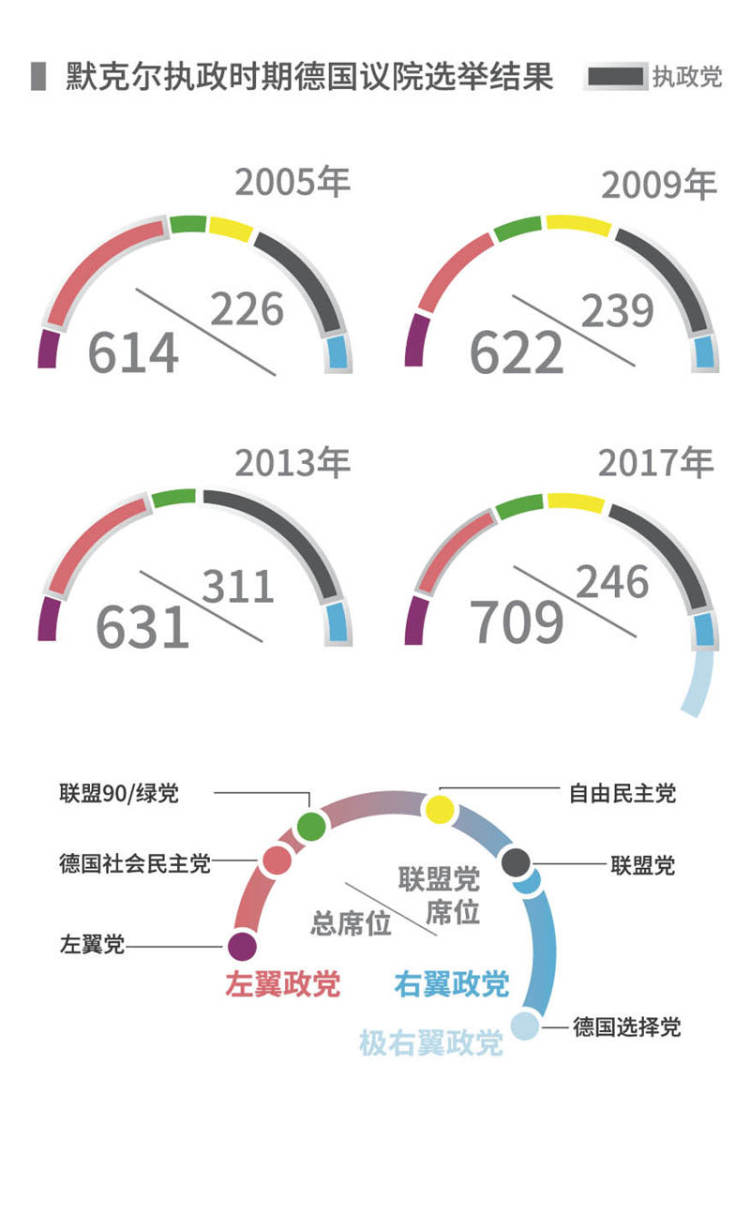
(郜超 绘制)
实际上,希腊本来可以选择直接退出欧元区,恢复独立的本币币种和财政自由,继而以相对较小的长期代价来化解流动性危机。但德国在“退欧”问题上表示了反对——倘若负债累累的希腊可以自行宣布退出欧元区,其他同样存在财政隐患的南欧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也有步其后尘的风险。欧元区的声望和稳定性将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这显然是高度重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默克尔所不能、也不愿接受的。是故在与希腊政府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中,德国方面对于纾困方案完全没有给希腊讨价还价的余地。
但早在1998年科尔担任德国总理时,正是对一体化前景信心十足的柏林力排众议,主动吸纳了并不被看好的希腊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三年后又“保送”希腊成为欧元区正式成员国。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柏林主导的欧洲货币联盟(EMU)始终让希腊享受极为低廉的借贷成本,使该国能够以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利率从外国借债。德意志银行(DB)前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迈尔曾经抱怨说:“德国好像在欧元区张罗了一桌大宴席,他们出售食物并提供贷款,结果客人们喝醉了、吃多了,默克尔手里攥着一大堆账单,开始抱怨不知该找谁买单。”
没有人怀疑默克尔身为政治“消防员”的才能。过去的16个年头里,她曾经在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克里米亚危机以及难民危机的交替考验下屡次转危为安,并使得德国始终扮演着欧盟双引擎之一的角色。她的绝佳心理素质和实用主义手腕,都是毋庸置疑的长处。但德国和欧盟之间层出不穷的问题也显示:单纯以经济收益作为中心的传统“欧洲主义”,正在遭受全球化逆转的考验。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