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刻装置《1划》(《40m》),20×4000厘米
版画与油画的“双重奏”
一进展厅,一条长40米的白色木刻线条的版画摆在墙边,像个巨大的箭头,指向展厅深处。这条长长的白线对面,悬挂着艺术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从1974年红卫兵主题的套色木刻,到后期逐渐成熟的抽象作品,沿着这条白线纵深开去,形成了谭平的创作轨迹。
这是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双重奏:谭平回顾展”展览的第一个展厅,策展人、艺术史家巫鸿在谭平的作品中找到的最鲜明的特质,就是版画和油画之间的碰撞,他称之为“双重奏”。谭平是学版画出身,又创作了大量油画,版画与油画从材料属性、技术方法、画面质感等各个方面都截然不同,而正因为不同,交错在一起有了一种张力。
这条40米的白线叫作《1划》,其实乍看上去非常简单,就是用一把刻刀在40米长的木板上刻画,再印出来,最终形成这样一幅“长卷”。2012年,谭平就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上展出过这件作品。中国美术馆主展厅是个圆形的大厅,这条白线就在圆形大厅里绕场一周,悬挂在墙上,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当时展出时,还引发过不小的争议。对于中国大多数艺术从业者来说,中国美术馆的圆形大厅象征着权威与经典,带着特殊的神圣感。《1划》贴着墙壁,形式又很简单,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却把圆形大厅包裹了一圈,喜欢这件作品的评论认为这是一种“顽童般的破坏式的作品”,带着后现代的反讽效果。
这一划看似简单,做起来远比想象中复杂。“一把圆口刻刀与一块长长的木板,如同决斗的双方,静静地等待开始的口令。”谭平在一段有关《1划》的自述中这样写道。这一场决斗要连续打6个小时,在这段时间中刻刀不停地在木板上行走,“所有的力量、经历,对艺术的理解,包括我内心的挣扎,全部留在刀和木板磕绊的瞬间”。

1987年的铜版画作品《视觉》,36× 29厘米
这像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我好奇这6小时会经历怎样的心理变化?谭平告诉我,其实从刻刀留下的痕迹中就能看到内心变化的波澜:“在开始的那一刻,脑子里的想法就有很多。比如一刀下去,刀法该怎么变化?刻多深?用多大力?是不是歪了一点?要不要再正一点?每一米都会有怀疑产生。”
谭平给自己的规定是10分钟刻1米,中间会有间歇性的休息,像是跑马拉松一样。他觉得艺术家已经做了很多即兴的事,有时候也要给自己一些规则,自己跟自己较劲。“其实我画这一条线,并不是想表达一个人从兴奋到感到疲惫、累的状态变化,而是想表达自始至终没有变化的感觉,也就是无始无终。那么,你就要保持这条线在呈现的时候,让人感觉到整个线条的完整性,所以你就得给自己制定一个游戏规则。”
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谭平创作了各个系列的作品。展览中也呈现了近年的“覆盖”系列,这是与版画并行的另一重奏——绘画。简单来说就是用颜料一层一层地涂抹在画布上,不断覆盖,不断改变画面的面貌,他觉得“一幅画画得越是完整,越漂亮,就越会激发他去覆盖和破坏的冲动”。
德国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格哈里·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也走过类似的道路,从具象到抽象,用颜料在画布上堆叠、融合,去探索形式和内心的共鸣。在1982年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他曾经这样阐释自己对看似毫无章法地刮涂颜料的理解:“当我们描述一个过程,或是拍摄一棵树,都会建立模式。如果没有模式,我们会对现实一无所知,沦为动物。抽象绘画是主观虚构的形式,它将不可名状却又真实存在的现实呈现在眼前。”
而对于谭平来说,无论是覆盖、滴墨还是刻线,任何一种形式也都建立在他自己的模式中,他也会将版画中的“模数”概念用在创作中,也就有了《1划》《一杯》《40×40》这些在游戏规则中的作品。

艺术家谭平
没有中国符号的东方气质
谭平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出身西方学院体系的抽象艺术家。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之后留学德国,在柏林艺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颇深,大量西方的书籍、绘画、思想涌入中国,成为那一代艺术家的现代启蒙。在这种启蒙下,谭平说自己那时候的作品黑白对比比较强烈,无论是版画还是绘画,这跟德国的艺术有相通之处,不是细腻温润那一派的。1989年,谭平申请到德国的奖学金,开启了5年的留学之路。
第二年,柏林艺大来了个央美的师弟刘野。谭平回忆道:“那时候大学是导师工作室制的方式,我跟刘野不是一个导师,教室也不挨着,但都在一层楼上,没事就喝喝咖啡聊聊天,谈谈各自的导师和最新的创作想法,挺开心的。”德国的几年学习为谭平和刘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们开始真正接受现代主义形式语言背后的独立、自由、理性的精神。
然而,从央美到柏林,看似相似的成长路径,两人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艺术面貌。刘野的心中始终住着一个孩子,他画得超现实,色彩丰富又形象乖戾,是一种可爱又有点邪恶或是悲伤的黑色幽默;谭平则完全不同,他的画从一开始就带着德国式的肃穆感,庄重而富有哲思,让人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他们走向了艺术的两个方向,表面上看是具象与抽象的不同,实际上一边是戏谑的游戏,一边是严肃的笃行。
这时的谭平画了不少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的作品,但他画面中的形象已经越来越简化,他开始从写实的景物中抽出几何形体,探索纯形式语言的表达方式。批评家易英在谈到谭平德国留学经历时认为,“不能说德国的教育彻底改变了谭平的艺术思想,因为在谭平的思想里本来就潜藏着自由的意识,形式本身就是自由的,它没有预定的模式,总是需要你自己去摸索与创造。谭平缺乏的是怎样把握形式创造的规律,德国的教育给了他最大的启示”。
虽然像赵无极、朱德群这样的华裔抽象艺术家早已在欧洲成名,但中国大陆的抽象艺术起步并不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大陆抽象艺术从崛起到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将欧美发展了七八十年的艺术形式浓缩在一二十年中进行。中国的抽象艺术虽然受西方影响很大,但大多数人也意识到了东方文化中的抽象内核,如何做出中国人的抽象艺术成了这批艺术家们共同的诉求。批评家黄笃将中国80年代的抽象艺术看作“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作心理”,是对主流的学院派和现实主义艺术的反抗,而到了90年代,他们更强调绘画的自我意识,或是注入中国式符号与文字,试图与商业绘画对抗,形成了抽象艺术的中国面貌。

《覆盖—黄色》,布面丙烯,160×200厘米,2013年
谭平就身在这股潮流中,但努力着不被潮流左右。2003年,谭平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手术后,医生从父亲身上取出肿瘤,用刀划开露出密密麻麻黑色的癌细胞,谭平被这种强烈的视觉刺激冲击到了。从那年开始,“圆圈”和“扩散”成了他创作的主题,大大小小的圆圈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由圆圈逐渐变为线条,呈现在不同颜色的底色上,记录着那段时间他的心路历程。“后来父亲慢慢康复,艰涩的笔触也就逐渐流畅起来,后来看看,还有些诗意。”谭平对那段时间的创作记忆犹新。也有很多评论指出,他的这种抽象中是有东方气韵的,但他不会把中国元素用在画面中,而是希望找到内在气质上的吻合。
2016年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谭平和瑞士艺术家卢西亚诺·卡斯特利(Luciano Castelli)一起做了一个艺术项目“白墙计划”。他们要用几天的时间,在500米的展线、1600平方米的两层美术馆空间的白墙上不断覆盖绘画,最终用白色颜料再涂抹干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需要面对绘画、空间、布局的各种挑战,又要在创作中破坏、消解、重生,人们会把这个行为的过程与禅宗联系在一起。谭平也认为,“当作品什么也不是时,就是它自己的时候,可能离真正的创造就近了”。
(本文图片由上海余德耀美术馆供图)
“我的抽象是有内容的,是具体的”
三联生活周刊:1987年你创作过一幅铜版画习作《视觉》,原本画的是一只很写实的鸟,但由于铜板腐蚀,形成了一些抽象的肌理效果,你也提到过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促成了你从具象绘画向抽象的转变。那么这个转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谭平:一开始画具象,都画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或场景,但随着越画越多,时间的积累,画面中的这些人和静物就会慢慢被消解。这么说好像也挺抽象的,我的意思是会越来越关注画的是什么,画里面是什么鸟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在自己内心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自己真正在画什么。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需要有一个契机去点醒你,这幅被腐蚀的《视觉》就是这个契机。而且我是学版画出身的,版画本身就要求艺术家有高度概括的能力,你怎么把自然中的形象、事物提炼出来入画,是很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过程中,你对绘画的理解发生了哪些改变?
谭平:我还是会在绘画中表达我自己的经历、感情,我自己的判断、观念,所以抽象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最终你会发现自己所看到的自己在一天天变化。画画对我来说,有点像照镜子,从年轻一直看到老,你自己看到的年轻的好,年老也好,喜悦悲伤这些,都会折射出你所有的生活经历,而这个个体的生活经历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变化,对我来说这几者之间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展览中,你会把一些不是同一时期创作的但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作品放在一起,为什么会这么做?
谭平:其实对我来说,这是对过去不同阶段的自己的一个比较。人的变化挺有意思的,你看从15到25岁会发生很大变化,无论是样貌上还是心智上,但从25到35岁的变化就挺小,至少不是特别表面的那种变化。人有时候确实在某一阶段就会突然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变,展览就是想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看到时间在中间起的作用。
所以我没有按照正常的时间线来安排作品的展陈,而是通过时间点的对比,让每一件作品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我一直想让我的作品活着,那活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与其他东西发生关系。这样一来在布展上就自由多了,可以不受时间线的约束,而是把变化的内在逻辑呈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理解抽象的?
谭平:对我来说,抽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抽象,而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个人化。比如我的一些作品,我喜欢保持那种很直接的表达,刻、画,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直接地表达出来,让这个作品更加有质感,让人能看到它的真实存在性。因为现在有很多作品,无论是摄影也好,数字技术作品也好,个人已经和作品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了,不会有这种实实在在的作品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而我还是想要去揣摩这种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我挺好奇在你的创作过程中,更偏感性还是更偏理性?因为可以在你的很多作品里看到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子,又有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但还能感受到作品里的控制力。
谭平:两方面肯定都有,通常在作品的构思之初都是很理性的,要设定这个创作的模式,这一部分都是很深思熟虑的。我希望我的规则是非常理性、清晰、有逻辑的,但是最终出来的结果是无法控制的。
这个有点像我经常举的例子,为什么足球那么吸引人?其实是规则做得好,很多运动员在其中可以发挥每个人的能量,而且结果不好确定,你总觉得他应该赢,但是最后别人赢了,足球的魅力就在这里。艺术也是一样的。在规则之下,我又很强调直接性,比如在做木刻、一遍一遍用颜料覆盖画布的时候,是比较随性的、凭感觉的。在规则中去找不确定性,才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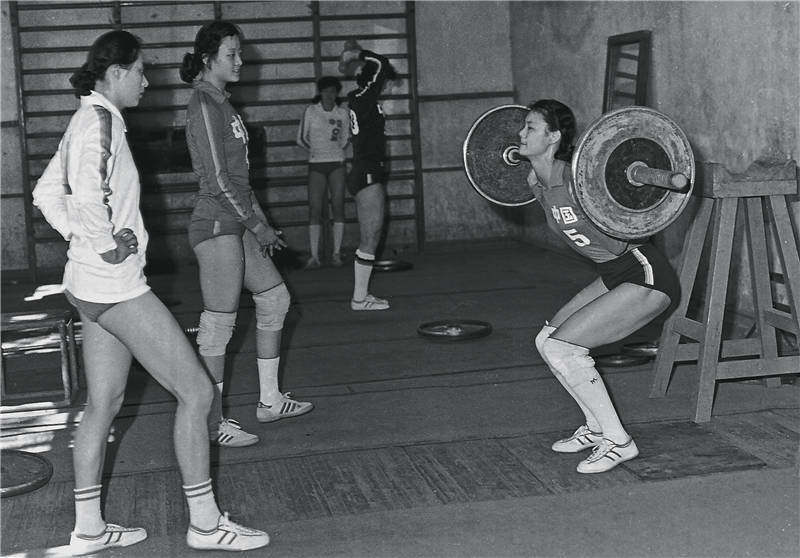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